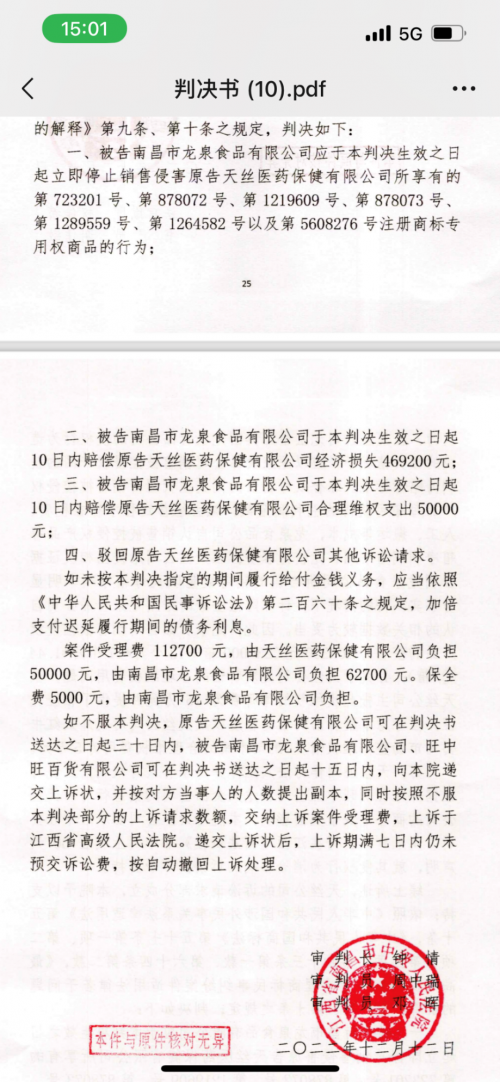媒介環繞之下,虛擬造物頻繁登場。
1月10日,百度舉辦Create大會,李彥宏親自站臺講解未來技術布局,足見其重視程度。
前期宣傳片中,百度AI數字人希加加以形象代言人的姿態引出本屆Create大會的主題。以技術的化身串聯技術的展演,百度做了有效的嘗試。
 (資料圖)
(資料圖)
但這次展示僅是淺嘗輒止,數字人作為點綴上場后便無下文,也隱約體現了當下數字人尷尬的現狀。
互聯網在現實世界的開發已近飽和,無論是移動終端的硬件水平還是用戶使用時間,都將達到現有技術條件下的極限。如何邁進虛擬世界,找到新的增量,數字人一度被認為是最普適的解決方案。
艾媒咨詢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虛擬人帶動產業市場規模和核心市場規模,分別為1074.9億元和62.2億元,預計2025年分別達到6402.7億元和480.6億元,增長態勢強勁。
越來越多的數字人被創造,企業開始以推出虛擬形象作為展示技術力的窗口。2022年的“數字名人”榜上,既有洛天依這種老牌虛擬偶像,也有柳夜熙、嘉然、冷鳶yousa等新生IP知名度漸起。
耀眼的數據難以掩蓋數字人產業發展過程中的磕磕絆絆,蓬勃生長的表象背后,若要追問其商業模式與應用邏輯,仍舊略顯模糊且充斥爭議。目前市場重點關注的交互性數字人中,成本與實用性的問題尚未解決,人格身份運營也多受詬病。
數字人是互聯網生態轉向的一個標志,作為更宏觀的元宇宙構想中的一環,需要引起一系列連接與關系的變化,以構建新的社會行動場域,開拓新的商業情境。
而目前的數字人應用很大程度上仍然困囿在舊有的邏輯,只是包裹了新潮技術的皮,缺少一些真正的、徹底的革新。
降本增效,有待檢驗
交互性數字人在市場應用中主要有服務型與身份型兩大類,服務型主要針對B端市場,將數字人看做高效智能組件,為企業提升產能、降低成本。
這種工具思維遵循著智能生產邏輯,數字人也確實有其功能優勢。直觀可感的視覺形象讓數字人區別于傳統的AI助手,可以作為數字員工替代真人服務,且通過智能技術驅動能夠完成簡單內容生產、提供相應服務。
人化形體的優勢在于,這類數字員工能夠介入的場景更為豐富,尤其在陪伴性服務業中能夠大量節省人力。因此,虛擬主播成為各大媒體重點投資對象。
2021年的數據顯示,中國直播人才需求量和人才缺口分別為1200萬和800萬,彼時就曾預測這一缺口在五年內還會持續增長。視頻與電商的火熱并未退燒,穿插其中的直播還在不斷擴大應用版圖。引入數字人理論上可以完美解決這一人才缺口問題。
一方面,數字人主播如果能實現高效復制、規模化生產,可以填補主播人才的空缺。同類型直播間的數據與智能處理模式直接批量應用,就能省去主播人才培養的時間與資金成本。
另一方面,數字人主播可以實現24小時全時在線,真人主播所不能覆蓋的特殊時間場景在數字人這里不成問題。此外,數字人的外觀表現與行為動態可以實時調適,“定制化私人主播”的概念也讓其更具有競爭力。
以京東云研發的AI直播數字人-靈小播為例,這款產品可應用于京東、快手、拼多多等直播平臺,通過智能驅動數字人在直播間實現商品介紹、實時互動、才藝表演等功能。
產品設計思路很清晰,挖掘非熱門時段的用戶增長,壓縮直播運營成本,以多變的數字人形象吸引關注。
理論上的可行性忽視了消費者的需求也在日益更新。
直播行業經歷了前些年的野蠻增長,內容同質化、主播交流技術不合格的直播間早已被市場淘汰。形成直播消費習慣的用戶相對從前更具主動性,會對直播主導者的業務能力多有挑剔,而這恰好是服務型數字人的痛點。
仿真程度有限,數字人機械化的動作模組與僵硬的語言反饋使其很難生產高質量的情感伴隨體驗。智能驅動程式單一,數字人也無法處理許多復雜問題或應對突發場景。
只能處理簡單場景,與其高昂研發成本之間形成了投入產出的巨大不對等。目前虛擬主播的實際應用多是以協助真人主播或偶爾出場增強話題與趣味性為主,真人員工與數字員工協同工作是較為現實的應用方案。要真正實現降本增效,數字人還有很大的技術與研發思路進步空間。
新瓶裝舊酒
相比于強調技術產能的服務型,數字人更大的野心在于面向C端用戶的身份型數字人。
“人格”是數字人區別于其他虛擬造物的核心點。
圍繞人進行的內容生產與信息輸出對于受眾而言有天然的矚目性與親和力。目前已經推出的身份型數字人主要集中在游戲、傳媒領域,通過打造虛擬偶像或虛擬IP,匯聚流量與粉絲,進而變現。
實際上,這類人格化營銷的思路并不新鮮,廣告營銷史上有過不少經典案例。利用人化形象搭建一個與消費者溝通的中介,從而與其產生社交層面的情感鏈接。“虛擬人形”可以在特定場景中與消費者持續互動,不僅有利于塑造產品形象、說服購買,更能夠創造出額外的符號價值,讓消費者愿意支付更高的溢價購買產品和服務。
玩轉這類運營思路的企業有很多,比如國人的一代童年回憶,海爾兄弟。27年前,動畫片《海爾兄弟》風靡全國,成為了家喻戶曉的IP,直到現在,海爾集團仍然在不斷更新這一虛擬形象的表現形式。成功打造一個IP能夠帶來極大的商業價值,不僅在圍繞虛擬形象展開的劇集中強化了品牌定位與科技標簽,又通過內容產品的傳播打開了知名度。
但身份型數字人的方向似乎跑偏了。
數字人的虛擬創制技術更成熟,表現形式也更加豐富,卻丟失了人格化運營的精髓。一是缺乏“人格”敘事,虛擬形象只是展現技術力的人形軀殼,沒有賦予其作為個體的獨特設定。
談論數字人的生成,話題總圍繞在技術表現力的升級。各家技術研發路徑不同,但都是朝著精進動態表現力上努力。虛擬形象在表情、口型、毛發、骨骼動態、布料實時演算等外形上精益求精,最終打造出的成品卻是一個精致的人偶,能帶來一時驚異,難以吸引消費者投注感情,建立“人際”聯系。
據艾媒咨詢調研數據現實,即便是深度二次元愛好者,虛擬偶像的垂直用戶,愿意為虛擬偶像消費的預期金額也集中在300元以下。
對比真實偶像產業的粉絲購買力,這個數字遠不夠看。而針對虛擬偶像的評價,有64.4%的用戶認為其缺乏感情,53.1%認為其缺乏獨特性。消費者對身份型數字人的整體印象停留在流水線生產的工業制品,數字人沒有創造新的文化消費選擇。
二是缺乏長期運營規劃。
IP不能速成,人化形象的敘事模式是動態的,一個完整的數字人格打造需要長期連貫的運營維護。不僅要在故事性、人設、話題點上持續更新,開發配套文娛產品、與消費者保持互動,也要對其技術基底進行維護和升級。然而現下初具知名度的數字人形象都缺乏“售后服務”,亮相的熱度過去之后,后繼無力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
拼圖元宇宙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講,數字人是最理想的元宇宙入口,通過與虛擬數字人的交互進行虛擬生產和勞動,形成虛擬世界的社會關系和結構。所以各大企業紛紛選擇以數字人入局元宇宙,搶下先手棋。
但數字人所遭遇的根本阻力與元宇宙相同,是現實世界的受眾還沒有完全準備好進入一個萬物皆媒,全面虛擬的數字世界。
這種落差可能體現在受眾對數字人仿真效果的接受障礙上。
比如恐怖谷效應理論提出,機器人外貌形象的擬人化程度越高,受眾對機器人的情感反應越積極,但當機器人與真人的相似程度到達某個臨界點時,受眾反而會覺得非常不適與反感。受眾對于“數字類人體”還存有現實-虛擬的認知隔閡,沒有跨越這個障礙,數字人無法真正落地,嵌入人類的生產與生活之中。
此外,虛擬的數字世界是一個整體系統,虛擬“人”“場”“物”的交互缺一不可,否則難以形成自洽的數字生態。
只有在沉浸式交互場景中,有充足的虛擬物品、虛擬貨幣這類物質資源,數字人才能充分發揮連接器的作用,盤活整個系統。這三者也是構建元宇宙所必須的拼圖。
而現在的情況是,數字人被孤立地拋擲到市場上,將其視作現實世界的“虛擬奇觀”進行售賣。不僅少有聯動虛擬場景建設與虛擬物質生產,也未強調其數字世界引路者的功用。
碎片化的展示與零散的交互體驗無益于數字人長遠發展,要進入集中訪問和消費虛擬體驗的元宇宙世界,數字人必須盡快擺脫“吉祥物”的身份。
總體而言,數字人是一項值得投資的生意。有政策扶持,有需求市場,可以集中實踐最新技術成果,也可以探索新的增長點,給元宇宙開發做鋪墊。
但當前的數字人實踐仍處于懸浮狀態,要想處理這個來自未來世界的命題,就得擺脫慣性,從全新的維度審視數字人的存在,思考數字人的未來。
關鍵詞: 市場規模超1000億的數字人 畫皮難畫骨